沙家浜茶馆叫什么,类似不眠之夜的话剧
沙家浜茶馆叫什么,类似不眠之夜的话剧?
雷雨
茶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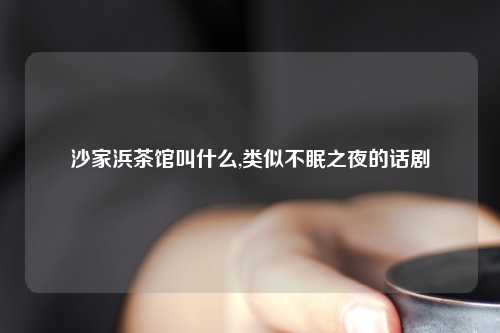
万家灯火
沙家浜
阿庆嫂出自哪篇文章?
阿庆嫂是出自《智斗》的人物形象。智斗是红色经典现代京剧《沙家浜》的一个片段,阿庆嫂是春来茶馆的老板娘,中共地下工作者。主要描写了阿庆嫂为掩护新四军伤病员,防止了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而展开的一番斗争。
阿庆嫂沉着冷静,不卑不亢,通过机智的对答,与国民党反动派代表刁德一、胡传魁巧妙周旋,最终化险为夷。
如何评价汪曾祺?
得罪朱自清,赖上沈从文,1个汪曾祺,赛过1000个段子手
汪曾祺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汪曾祺
就算不知道汪曾祺的人肯定听说过一句话:“人走茶凉。”这话就是汪曾祺发明的。
在近代文学史上,汪曾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不仅因为文章写得极好,还因为先生身上有着文人雅士们失落已久的、诗意的生活趣味。
贾平凹说:“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梁文道说:“像一碗白粥,熬得更好。”
沈从文说:“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江苏北部有一个不大的城市——高邮,这是一个水乡,在长日流水的运河旁。
1920年3月5日,恰逢元宵节,汪曾祺出生于此。
生于斯长于斯,此后一生,汪曾祺生命中始终活波泼地流淌着清澈、通透、有趣与涵养。
汪家算不得望族,但也是个殷实的书香世家,祖父是儒商,到他出生时,家里已经有两三千亩田,还开着两家药店,一家布店。
汪曾祺少孤,3岁没了娘,但一家人都疼他。
1925年,5岁便入了幼稚园学习。在那里,汪曾祺遇到了一位亦师亦母、终身难忘的人:王文英老师。
王文英见汪曾祺小小人儿戴着妈妈的孝,十分心疼他。这个幼稚园实际上只有一个女教师,教唱歌、跳舞都是她。
56年以后,汪曾祺回到故乡,去看望怀念一生的王老师。
“我今老矣,愿吾师康健,长寿无灾。”
虽生于动荡年代,汪曾祺的童年却惬意得很。
在孙辈里,祖父比较偏爱汪曾祺,亲自教他习字,教他读《论语》,每临寒暑,还请儒生为他讲解古文。
汪曾祺从小显露出的才气,让祖父得意不已:“如果在清朝,你完全可以中一个秀才!”
那年,汪曾祺才13岁。
他的父亲汪菊生,更是个极有趣的人:善绘画、刻图章、弹琵琶、拉胡琴,做菜、打拳、单杠体操、祖传治病,亦是精通。
初中时汪曾祺爱唱戏,唱青衣,他的嗓子高亮甜润。在家里,父亲拉胡琴,他唱;
十七岁初恋,在家写情书,父亲在一旁瞎出主意;
十几岁时和父亲对座饮酒,一起抽烟。
人生何其有幸,多年父子成兄弟。
父亲的才学和秉性,自汪曾祺少年时,就挂起了一盏温润的灯。
1926年秋,汪曾祺到县立第五小学读书,从家到小学要经过一条大街,一条曲曲弯弯的巷子。
汪曾祺每次放学回家,总喜欢东看看,西看看:
看看那些店铺、手工作坊、布店、酱园、杂货店、爆仗店、烧饼店、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
看银匠在一个模子上錾出一个小罗汉;
看师傅怎样把一根竹竿做成筢草的筢子;
瞧车匠用硬木车旋出各种形状的器物;
看灯笼铺糊灯笼……
这些店铺和手艺人让汪曾祺深受感动,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他的记忆。
“我的小说有很多篇写的便是这座封闭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
由于文学对汪曾祺影响很深,上小学后不久就显出偏科现象,对语文越来越喜欢,对算术却顺其自然地放松了。
从三年级起,汪曾祺的算术就不好,一学期下来勉强及格,语文却总是考全班第一。
几何老师曾评价说:“阁下的几何乃桐城派几何。”
意思是他的几何作业常不经论证就直接跳到结论。
不过在“五小”,汪曾祺是风光的,他除了语文好,写字好,画画也好,这“三好”使他在全校才名大响。
1932年,12岁的汪曾祺小学毕业,考入高邮县初级中学读书。
高北溟教国文那几年,汪曾祺的作文几乎每次都是“甲上”,在所授古文中,汪曾祺受影响最深的是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
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1935年秋,汪曾祺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
这是一座创立很早的学校,当时这所学校注重数理化,轻视文科。喜爱文学的汪曾祺便自买了一部《词学丛书》,课余常用毛笔抄写宋词。
读到高二年级,日本占领江南,江北危急。
汪曾祺不得不告别南菁中学,并辗转借读,但学校的教学秩序都因战争打乱,汪曾祺勉强读完中学。
战事日紧,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在离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在庵里大概住了半年。
半个世纪后,他在小说《受戒》里描写过这个小庵。
在这座小庵里,汪曾祺除了带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外,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本是上海一家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
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他的终身。
父亲那时也看了沈从文的小说,惊讶于:“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
汪曾祺和沈从文
1939年,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大学。
一到昆明,便住进了医院,那是他一生第一次住院,也是惟一一次。
高烧超过40度,护士注射了强心针,汪曾祺问她要不要写遗书?
经过治疗,汪曾祺刚刚能喝一碗蛋花汤,便晃晃悠悠进了考场。
交完卷,一点把握没有。
但汪曾祺居然考中了第一志愿: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汪曾祺之所以不远千里奔赴昆明,就是冲着被誉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中文系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著名学者。
可直到大学二年级时,汪曾祺才正式拜见了他景仰已久的沈从文先生。
汪曾祺把沈先生开的课全都选了,包括选修课。
汪曾祺写过一篇小说,他尽量把人物对话写得有诗意,有哲理,沈从文看了后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
沈从文常常教诲学生:“要贴到人物来写。”
这句话对汪曾祺影响很大。
沈从文最喜欢汪曾祺,他曾经给这位学生的课堂习作全班最高分——120分!(满分100分)
汪曾祺早年写的作品,都是沈从文代他寄出去投稿发表的。沈从文还处处对别人说,汪曾祺的文章写得比自己还要好。
沈从文有课时才进城住两三天,汪曾祺都会去看他。还书、借书,听他和客人谈天。
沈从文上街,汪曾祺陪他同去,逛寄卖行、旧货摊,买耿马漆盒,买火腿月饼。
饿了,就到沈从文的宿舍对面的小铺吃一碗加一个鸡蛋的米线。
有一次汪曾祺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从文以为是一个生病的难民,一看,赶紧和几个同学把汪曾祺架到宿舍里,灌了好些酽茶。
有一次汪曾祺又去看沈老师,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沈老师一言不发,出去给汪学生买了好几个大橘子。
沈从文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汪曾祺写了他平生第一篇小说《灯下》。这篇习作在沈先生指导下几经修改,便成了后来的《异秉》。
然而这位沈老师的得意门生,却是个非典型性学渣:
他在联大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儿郎当,高兴时就上课,不高兴就睡觉,上课很少记笔记,并且时常缺课。晚上泡茶馆或上图书馆,把黑夜当白天。
对于不感兴趣的课,更是素来不去。朱自清讲课以严肃闻名,要求学生仔细记笔记,汪曾祺不太适应,时常缺课。
后中文系主任想让朱自清收汪曾祺做助教,朱自清一口回绝了。
“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我的助教呢?”
闻一多教唐诗,把晚唐诗和印象派的画结合在一起讲课,对汪曾祺启发很大。
汪曾祺替一个学弟做“枪手”,写了篇李贺诗的读书报告,大意是:别人是在白纸上作画,李贺的诗则是在黑纸上作画。
闻一多看了大加赞赏,评价说:“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
战乱时,因邮路中断,汪曾祺一度失去了家里的接济。虽然穷得叮当响,但他日子过得滋润极了。
有钱时,吃好馆子,什么汽锅鸡、锅贴乌鱼、铁锅蛋、腐乳肉之类,全吃了一个遍。
没钱就吃米线、饵块,他什么品种的米线都吃过。
大二那年,汪曾祺失恋了,两天两夜不起床。好友朱德熙吓坏,挟一本厚厚字典火速赶往46号宿舍。
“起来,吃早饭去!”
于是两人晃悠出去,卖了字典,各吃碗一角三分钱的米线,全好了。
离开大学后,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观音寺一个由联大同学办起的“中国建设中学“里当教师。
那时汪曾祺与同在任教的施松卿相识,一爱便是一生。
施松卿生得眉清目秀,老爱生病,联大同学叫她“林黛玉”。
在中学教书连饭都吃不饱,他们依然“穷快活”。
没有肉吃,汪曾祺就学工友用油爆豆壳虫,一尝,居然有盐爆虾的味道!
施松卿不知从哪捡了匹马,多年后,汪曾祺还记得她牵马散步的那一幕:
一个文文弱弱的年轻女子,在黄昏的天色中牵着一匹高高大大的马在郊外漫不经心地散步,漂亮极了!
1946年初秋,汪曾祺从昆明远途跋涉到上海。
在上海,汪曾祺成了“沪漂”,找不到工作,只得去朱德熙家寄居,一度写信给老师沈从文说想自杀。
沈从文回信骂他,然而骂归骂,最后还是沈从文托李健吾帮他找了一份教职,到民办中学教了两年书,直到1948年初春离开去往北平。
在此期间,汪曾祺写了《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小说,结为《邂逅集》。
汪曾祺到北平后才发现,在那里立足不易,找工作更不易。
他临时借住在北京大学,失业半年后才在北平历史博物馆找到工作。
陈列室在午门城楼上,展出的文物不多,游客寥寥无几。职员住在馆里的只有汪曾祺一人,他住的那间据说原是锦衣卫值宿的屋子。
为了防火,当时故宫范围内都不装电灯,汪曾祺就到旧货摊上买了一盏白瓷罩子的古式煤油灯。
晚上灯下读书,不知身在何世。
在北京市文联工作的时间里,独具慧眼的老舍先生时任北京文联主席,他发现了汪曾祺的创作才能,曾预言:
北京有两个作家今后可能写出一点东西,其中之一便是汪曾祺。
汪曾祺创作出京剧剧本《范进中举》,最初无人过问,被搁置一边,许久之后被王昆仑偶然发现,推荐演出后效果甚好,这才引起人们的重视。
1945年,汪曾祺被调至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写《民间文学》。
编杂志时,他刊发过很多好稿,把陈登科的《活人塘》从废稿堆里“救活”了。同事们都觉得他鉴赏水平一流,却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个作家。
从1950年到1958年,汪曾祺一直当文艺刊物编辑,也辍笔不写了。
后来下放后,因为他画的好,安排让他画画,他每天一早起来,就到地里掐一把马铃薯花,几枝叶子,回到屋里,插在玻璃杯里对着描画。
还赋诗云:“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
马铃薯花落后,就画成熟的薯块,生活单调而漫长,他却自个儿找乐子:
画完了,就丢在牛粪火里烤熟吃掉,还一度自嘲:“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这么多品种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无论生活如何,他骨子里的情趣与雅度却一直都在,对生活,永远怀着天真的热爱。
1979年第11期的《人民文学》上,登了篇汪曾祺的《骑兵列传》,这时他已59岁,才开始以写作闻名于世。
从那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写出了《受戒》《大淖纪事》等作品。
汪曾祺长时间没有书房,得在小女儿的屋子里写作。
女儿汪朝下了班在睡觉,汪曾祺急着要写文章,又不敢进屋,憋得满脸通红到处乱转。
儿女们和他开玩笑:“老头儿,又憋什么蛋了?”
一开始,汪曾祺还辩解说是写文章,不是下蛋,后来也常笑着说:“别闹,别闹,我要下蛋了。这回下个大蛋!”
汪家长期住在单位分配的房子里,房子很窄小,外国友人来访,见“国宝”级的作家居然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差点没掉下眼泪。
家人让汪曾祺写个申请住房的报告,他半天也写不出一句话来,末了扔出一句话:“我写不出!我不嫌挤!我愿意凑合!”
有人劝他写点宏大的文章,他回答:“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汪家一直挂着幅高尔基的木刻,有天汪曾祺突然提出:“把这个取下,换上我的照片。”
儿女们都笑了,老头儿自视挺高。
汪曾祺嗜吃的名气,正是因为他写了课本上那篇《端午的鸭蛋》。
在西南联大时,汪曾祺早已吃遍了正义路的汽锅鸡、东月楼的乌鱼锅贴、马家牛肉店的撩青、吉庆祥的火腿月饼……
逛集市,他赖在摊边吃白斩鸡,起个名目,叫坐失良机(坐食凉鸡);
下馆子,他和老板唠嗑,听各乡趣闻,偷学后厨做菜;
要是没课,他就溜到某不知名的小酒馆,要上一碟猪头肉,咂一口绿釉酒,赏馆外碧叶藕花,听檐上昆明的雨。
在江阴读书时,他听说过河豚的美名,总想一尝,奈何未能如愿。多年后写诗:“六十年来余一恨,不曾拼死吃河豚。”
汪曾祺老了之后更是个可爱的“老顽童”,贪吃、贪喝、贪看、贪玩儿,贪恋人世间的酸甜苦咸。
只因别家闺女随口一句:“黄豆是不好吃的东西,汪伯伯却能做得很好吃。汪伯伯是很厉害的人。”
他就咧嘴哈哈笑。
不仅爱吃,汪曾祺也喜欢做美食。
汪老女儿朋友来,汪老亲下厨房,忙活半天,端出一盘蜂蜜小萝卜。
水嫩嫩的小萝卜削了皮,切成滚刀块,蘸上蜂蜜,插上牙签。然而客人一个没吃。
有一年,汪曾祺患了急症——胆囊炎发作。
确诊后,女儿问大夫:“今后烟酒可有限制?”
大夫摇头:“这个病与烟酒无关。”话音刚落。
老爷子就嘻嘻哈哈,捂嘴窃笑起来。
谈起父亲,女儿笑着说,“他在我们家是非常没有地位,我们这些子女都欺负他,妈妈也完全不拿他当回事,但他乐在其中。”
平日里,他酒一喝多,就给自己争地位:“喂喂,你们对我客气点,我将来是要进文学史的。”
人人皆知汪曾祺爱吃,可他谈起吃来都是寻常吃话,读来却是百看不厌。
家乡的双黄鸭蛋,北京的豆汁儿,湖南的腊肉,江南的马兰头,朔方的手把肉,昆明的牛肝菌、汽锅鸡……
因为他吃遍天下,又长于观察,一个不起眼的食材往往被他描写得格外细腻。
有人说他是“作家里最会吃的,也是厨师里最会写的”。
有读者开玩笑说:“饿得时候根本不敢读,跟舌尖上的中国一样。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离世。
作别前,他想喝口茶水,便和医生“撒娇”:“皇恩浩荡,赏我一口喝吧。”
医生点头应允,他便唤来小女儿,“给我来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
龙井尚未端来,斯人却已逝。
你看过哪些让你毕生难忘的电影?
让我毕生难忘的电影是作家路遥的小说改编的《人生》。它是真的改变我人生的一部电影。三十年后的今天,每当我回看《人生》时,仍然感慨万千。
因为,我曾经就是电影里那个真实的高加林,只是我最终没有忘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没有选择背弃良心抛弃那片土地和那个深爱着我的“巧珍”,这真要感谢《人生》这部电影。
正如路遥原本给《人生》的电影剧本书写的片头词:“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1982年,我高中毕业高考落榜,回到那个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但始终不甘心地在迷茫中寻觅着跳出农门的出路。秋季的一天,二婶给我介绍一个对象,是邻村的一个姑娘,长的圆圆脸、大眼睛,壮壮实实的,我娘一看就喜欢地说“能干活、能生儿子,肯定是个好媳妇”,于是定了婚。1982年底我当兵到了部队,1984年考入石家庄陆军学院,成为一名军官。这在我们那小山村就像古代时中了状元一样,引起七大姑八大姨的夸奖和上下邻村乡亲的羡慕甚至嫉妒。
然而,那时的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我每天想的是自己已经是个堂堂的军官,怎样才能甩掉家里那个土里土气的村姑未婚妻呢?到军校报到后,我便开始实施我的计划,就是不再给未婚妻写信,让她知趣的主动提出分手。善良的未婚妻相信了我训练紧没时间的托词,没有任何怨言的照顾着我的父母。寒假来临,我经过一个学期的酝酿和准备,决定回家和未婚妻摊牌,解除婚约。
回到家的当天晚上,正好村里放电影,电影名就叫《人生》。电影里那个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简直就是我自己的化身,勤劳善良的刘巧珍对高加林真诚的痴爱,虽然自己的悲剧是高加林制造的,但她仍然毫无保留全心全意爱着高加林。
而高加林和我一样的不再满足于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和我一样的渴望走出农村,改变自己的命运。正如高加林说过的那样:“我,一个农民的儿子,从穷困乡村来到城市。我知道,这次进城,再不是一个匆匆过客了,我已经成了这个城市正式的一员。我的理想的风帆,就要从这里开始启航……”高加林的灵魂在情感与理智的撕扯中挣扎着、呐喊着,字字句句精准地击中我的心坎,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然而,随着故事的推进,到电影结束时,善良的巧珍阻止大姐对灰头土脸地卷铺盖回家的爱人的报复行动,并哭着说“不管怎样,我心疼他;要是你这样整治家林,就是拿刀子痛我的心哪!”看到这里,我震撼了,不由自主地泪流满面。。。电影在浓郁的黄土地民俗中展现出的悲剧之美,让人不忍卒看。浓郁的民歌氛围和情调,让人觉得悲凉而伤感,一曲《走西口》贯穿影片始终,让人心情复杂而沉重。
电影中,刘巧珍是中国千年乡土文化滋养起来的美和善的化身,就象我的未婚妻一样,孝顺、纯朴、宽容。而自己就像高加林一样迷失在时代的洪流中,用剧中德顺老汉的话说就是:“把良心都卖了、成了嫌弃乡土气息的豆芽菜”。突然,一个声音在我心底发出:我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生在这儿长在这儿的农村娃,不能嫌弃这片土地和这些勤劳朴实、深深爱着我的人,更不能出卖自己的良心和初心。那晚电影散后回到家,我对未婚妻说,等我军校毕业了咱们就马上结婚。就在那晚我做出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至今记忆深刻的是,影片中的出现最多的各种各样的路:林荫小路、村里的乡间小路、盘旋在山中的盘山公路、平坦的土路、宽广的柏油马路···不同的路将人带向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未来,就像人生的路,到处都是岔路口,是选择不忘初心、还是迷失歧途,就看自身的抉择了。
如今,我和妻子已幸福生活了三十年,我从未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在我人生的重要路口,是《人生》这部电影使我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才使我走到了幸福的今天和拥有美好的明天。
沙家浜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1、芦苇迷宫
沙家浜芦苇活动区是整个景区的核心,分成水上和陆上芦苇迷宫两大区域,纵横交错的河港和茂密的芦苇,构成辽阔、狭长、幽深、曲折等多种形态的水面或陆上芦苇空间,形成一个个迷宫,为游客提供了一个追寻野趣和体验新四军辗战芦苇荡情景的场所,有诗云:“浅水之中潮湿地,婀娜芦苇一丛丛;迎风摇曳多姿态,质朴无华野趣浓”。漫步、泛舟其间,苇香扑鼻,野趣横生。
2、影视基地
横泾老街影视基地保存了农村建筑旧貌,吸纳江南小镇精华,重现了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的江南乡间风貌和文化特征。三十集电视连续剧《沙家浜》就是在这里完成的,此外还有《三言二语》、《金色年华》、《中国酒王》、《茉莉花》等电视剧到此取景拍摄。横泾老街影视基地每天定时有挑花担表演和婚俗表演,此外,京剧《沙家浜》每天准时上演。
3、国防教育园
沙家浜国防教育园位于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北侧,占地130亩,由拓展训练区、彩弹射击区、军事武器展示区、抢滩登陆射击场、户外野营帐篷区等部分组成,是沙家浜风景区为增强公民国防观念,普及国防知识,增强旅游可参与性,全面提高青少年素质而建设的又一新的亮点。
4、春来茶馆
春来茶馆再现了当时遍布沙家浜村落的小茶馆原形,“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竹林嬉戏、听戏品茗,尽享农家生活乐趣,与芦苇迷宫相得益彰。良好的大自然生态,是追求回归自然“绿色旅游”的极佳选择。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