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衣大炮,清代的红衣炮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
红衣大炮,清代的红衣炮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
天启六年,在袁崇焕坐镇的宁远城,后金军来势汹汹,势必要拿下此地,然而旋即败退。明朝“朝野欢呼,士庶空巷相庆”。
号称天下无敌的后金军为什么会突然退军了呢?原来,是这里出现了一个他们见所未见、令他们失魂落魄的大杀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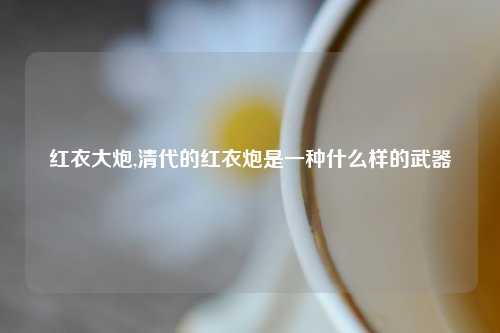
据《明季北略》记载,当时袁崇焕在宁远城共拥有西洋大炮11门,火力可覆盖城外270度的范围;相邻大炮还可相对射击,全面无死角。重炮攻击下,后金军损失惨重。
《石匮书后集》记载:“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
明军拥有这种大炮的来历也很偶然,万历48年,一艘荷兰武装商船沉没,广东当地政府组织打捞,其中最大收获便是那些长身管、纺锤形结构的前膛加农炮。
经过工匠们的认真研究和改进,将西洋炮改为铸铁炮身,在炮管外铸铜的新型大炮,有效降低了炸膛的风险,经久耐用。这种大炮重量轻,管壁薄,故而炮弹也可以做的更大一些。
明朝在天启年间又铸造了十四门这种炮,同时从澳门购入了一些大炮,到宁远大战之前,明军能使用的大炮一度接近40门。
《明史》中对此炮的威力介绍不惜笔墨和措辞:“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而明末文学家张岱则更为夸张:“一炮糜烂数十里”。当然,它的射程在其时还无法达到数十里的,这里只是文学家的一些夸张之词罢了。
但不可否认,作为最先进的炮种,它的威力给与双方的震撼都是极大的。守城军民目睹了它的威力后感慨:
“似兹火器,真所谓不饷之兵、不秣之马,无敌于天下之神物也!”
对这种大杀器,明军将其称为“红夷大炮”,虽然有的是从葡萄牙人手中购入,但却是荷兰人制造的。红夷是因为欧洲诸多国家来到明朝的时候皮肤泛红,军民将他们叫做“红夷”。因后金-满清忌讳“夷”之说,将其改为红衣大炮。另外一种说法是明军常在大炮上罩上红衣,故名”红衣大炮”,
红夷大炮是统称,并不是只有一种型号,千斤以上称为西洋一号炮,千斤以下称为西洋二号炮,500斤为中炮,320斤为小炮,参数的不同,威力也不同。
后金军经过了宁远大败,一是彻底知道了这种新式武器的巨大威力,二是产生了觊觎之心。为避其锋芒,后金利用骑兵坚忍和灵活快速的优势,疯狂穿越红衣大炮的落弹区,在炮火的间隙期,冲杀到明军阵地。如此一来,便有多场胜利,明军独有的红衣大炮作为战利品,就这样落入了后金军的手中。
另外,在崇祯六年的四月,孔有德、耿仲明等投降后金,他们精通火器操作,甚至精通红衣大炮的制造过程,同时,还带来了多门现成的红衣大炮。
后金军有了红衣大炮,再加上后金军的步骑结合产生的优势,在后续的战斗中,攻城拔寨,所向披靡。后金攻打李自成的潼关天险时,红衣大炮便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古代大炮如何击中目标?
兔哥回答。古代火炮的应用,自从黑火药出现,就被用于军事,早期的火炮是用火药发射弹丸,或是把铁渣添入火炮炮膛,利用火药爆炸的压力把弹丸或这些铁渣推出炮膛。古代火炮属于一种口径和重量都较大的金属管形射击火器,其由身管、药室、炮尾等部分构成。滑膛炮膛,多采用前装火药和弹丸,可发射石弹、铅弹、铁弹和爆炸弹等,大多配有专用炮架或炮车。 古代火炮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而伴随这个发展过程,射击方式,射程,精度也有所提高。古代早期火炮的射程通常在300米左右。而明代时出现了进口的火炮,如佛朗机,红夷大炮等。佛朗机的射程可以达到2000步(古代以步数测量射程),大概可以达到1800多米。而红夷炮具说可以达到上万米,这个相当高了。(下图佛朗机)古 代火炮怎样使用。古代火炮的攻击目标的方法和现代火炮有很大不同,火炮要想打击目标就必须先要瞄准,这是火炮首先必须要做的最重要的一步,无法瞄准就无法击中目标。(下图,佛朗机) 古代火炮没有现代火炮这样的瞄准机构,甚至连简单的瞄准具都没有靠什么瞄准?其实古代火炮的瞄准就是利用火炮的身管为指向轴心进行瞄准,这个靠经验的成分很高。另外从古代人测量射程时用到了“步数”,这就等于古代火炮是有射程概念的,而且,古代火炮上有可以上下活动的炮耳轴,这也说明古代人是通过火炮的仰俯角度来设定火炮的攻击距离。打击目标时,通过有经验的炮手负责瞄准,靠经验,和目测方式,调整火炮仰俯角度,对目标进行射击,然后根据命中点对火炮进行修正。 古代火炮的性能,古代火炮不具备对目标的远距离定位打击功能,只能是概略性的打击,在古代这已经是很先进了。以上的方法也是古代火炮打击目标的方法。即便是现代的火炮,有现代化的制导,瞄准设备也不能做到100%的命中率。
以上是个人的观点,欢迎指正,相互探讨,也欢迎你的阅读。(图片来源网络)
眀朝主力船能装多少门大炮?
众所周知,随着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欧洲海上力量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而在遥远东方的明帝国,自从郑和七下西洋之后,四海平静,漫长的海岸线上一片祥和。没有压力也没有需求,在北方蒙古人的边防侧重之下,海防自然而然就被搁置一旁。乃至于到嘉靖前期,明帝国海防破碎、武备糜烂,战船十不存七、士兵大量逃亡。最终,嘉靖中期倭乱大规模爆发,明朝在如此情势之下不得不重整海防。
当时的日本船只
其实倭寇并非凭借有多么强大的海上势力,他们不过是类似于从海上入侵的游牧民族,主要目的是深入内陆劫掠财富,因此并不会主动选择在海上跟明朝水师硬碰硬。倭寇往往驾驶着轻便迅捷的中小船只,迅速突入近海登陆,然后四分五散各自劫掠。在没有雷达的年代,很难在海面上对其进行有效拦截。比如,俞大猷就曾经驾驶大船因为速度不及倭寇小船以及吃水太深,只能无奈的看着倭寇从浅水区逃走。
在这种情况下,明军为了能够有效堵截已发现的倭寇船只,只能把大船改小,400料战船改成200料,并一改再改为150料战船、100料战船,为的是避免发现了也追不上。因此,明军在对付倭寇这种敌人的时候,一般以中小船只为主,大船也就局限于9~10丈长的福船和广船类战船,火器还是以传统的火砖、火球、火箭、碗口炮等纵火类和臼炮类火器为主,再加上少量佛郎机和一门四五磅的舰首发熕炮,便足以对倭寇船只产生碾压级别的优势!
明嘉靖时期福船配置
但上述这些也只能够对付海上力量不强的倭寇和小股海盗罢了。而且这种类似治安战的模式,其实对海上力量的发展极为不利。后面由于西方势力的进入,中国海盗们能够先于明军更快的接触到西式火器,他们占岛为王、招募工匠、走私铁器硝黄等等,从而积累了大量势力,再之后铸造火炮、建造船只,一时间在嘉隆万时期的明朝海面上涌现出了诸如林道乾、曾一本、林风、朱良宝等名噪一时的大海盗。
这其中又以曾一本实力最为强大。他拥有战船数百艘、兵卒数万人,为祸东南。他还拥有一支由东莞大乌尾船组成的主力舰队,这些乌尾船载重都在万斛以上,换算成今制其载重在380~400吨之间。这种实力已经超过了以往明军水师所面对的任何敌人,因此明军也开始作出调整。为了剿灭曾一本,东南沿海29个县在半年内,建造了24艘15~17丈长,船体覆盖一层铁甲的封舟战舰,此外还有一百多艘大福船。这可以说是自郑和之后,明军最为强大的海上作战力量了!
明代封舟
而除了船之外,海盗们装备的大量火炮也给明军带来不少麻烦。胡宗宪在《筹海图编》中直言,“海寇所恃全在于铳,吾亦以铳为应”。当时明军的策略为“以船之大者为中军座船而当其冲,以船之中者为左右翼而分其阵,以船之小者绕出于前后两旁之间”。装备则“中军大船之前,仍用次等船载佛郎机大铳数架以镇之。两翼中船之前,亦再次用船装载铜将军大铳数十架以列之,其小船亦各载鸟铳铅铜数百以备于四面。”
明军舰队立营图,1为座船(中军大船);2为中船(中军大船之前次等船);3为哨船(中船之前再次等船)
结合《兵学指南》就不难理解胡宗宪这段话了。他根据船型大小和作战任务的不同分为四种船,即座船(中军大船)、中船(中军大船之前次等船)、哨船(中船之前再次等船)、小船。座船就是中军大船即旗舰;中船就是大船之前次等船,即座船周围的五艘中军中船(数架佛郎机大铳镇之,保护座船);中船之前的次等船自然就是外围的哨船(铜将军大铳数十架,作战主力);小船就是在各船旁游弋骚扰的小型船只,装备鸟铳喷筒数百枝。
以战舰十六艘为例,舰队分三行横列,十艘哨船装备数十架铜将军大铳,火力最强,处于第一行;五艘中船负责护卫座船,在座船之前哨船之后第二行,座船作为旗舰主帅,则位于最里面第三行,而且五艘中船处于十艘哨船间隔空间之后,并不阻碍火力投射,因此第一行和第二行可以同时开火发挥最大火力。即座船前中船镇之,中船前哨船列之,这也符合《筹海图编》里“每数船列为一行,每一阵列为数行”的描述。
明军舰队作战图
到了明朝末年,荷兰人屡屡入犯沿海,更是与明军爆发了南澳海战和澎湖之战。加上更加强大的郑芝龙、刘香等海上势力崛起。其中郑芝龙的顶级战舰拥有西式火炮30门,刘香的大船也装备有十几门红夷炮,因此明军水师不得不再次进行升级。这时候的明军水师开始出现双层甲板炮舰与单层甲板炮舰,并在侧舷装备西式火炮10~30门不等。英国人彼德·芒迪在珠江口就曾遇到一艘载炮28~30门的明军双层甲板炮舰和一艘10~11门火炮的单甲板小炮舰。
珠江口明军战舰
而对于明军双甲板炮舰记载最为详细的当属崇祯本《兵录》,书中记载“焚寇之舩莫如火,碎寇之舩莫如炮,大抵舩宜极新坚为佳,大固好,亦不必太大,随海上双桅皆可用也。将此舩下层左右约开铳孔,或三十处,或二十处,安置红夷大炮,每门重二千三四百觔者,用一车轮架乘之,便於进退装药。此等大炮,每舩一只或六门,或八门,左右排列;余孔亦列千觔与五百觔之铳,必要五百觔为率者,方沉重不跳且送弹端直。至上层战坪如用百子狼机等炮。大约一舩要兵百余名,大小铳共五六十门,多多益善。”
日本绘唐船图
以此可知,明军双甲板炮舰分为大小两种,大号炮舰下层甲板配置红夷炮8门,千斤炮与五百斤炮22门,上层甲板用佛郎机百子铳等小型火炮30门,共60门;小号炮舰下层甲板用红夷炮6门,千斤炮与五百斤炮14门,上层甲板用佛郎机百子铳等小型火炮30门,共50门。无独有偶,崇祯时期的南京工部郎中董鸣玮,他也曾仿照闽海战船建造了两艘江防炮船,名为“龙骨炮船”。该船共配置火炮18门,其中红夷炮8门、百子铳10门,因为是江防战船,因此可能要比原型闽海战船略小一些。
船上用500斤红夷炮
除了兵书记载外,在明朝档案里还有这么一条史料。崇祯十三年(1640),浙江在围剿海盗时,明军使用了装备西式侧舷火炮的战舰,双方在海上遭遇后用火炮互相对射了七八个小时,最终明军获胜,俘获了大、中船只41艘。其中大船26艘中船15艘,全部被改编进各寨明军补充水师力量,之后明军又调拨红夷炮、神飞炮、威远炮、百子铳各项火炮共一千六百五十八门装备这些战船。这样平均一下就会发现,这41艘战船每艘都能分到40~42门火炮,不过毕竟大小不同,所以如果按照尺寸来分,那么26艘大船完全可以分到50门火炮,剩下的15艘小船也可以分到22~23门火炮。
其中百子铳是用来攻击敌方甲板人员的,炮弹重30两,2.5磅左右;威远炮为冷锻炮,所以重量很轻,只有200斤左右,但炮弹却重3.6斤,在4.5~5磅之间;神飞炮重1050斤,装火药6斤,炮弹重量没有记载,不过如果按照1:1弹药比来估算,炮弹应该在6斤左右,合8磅;至于红夷炮,那范围就很大了。从4斤弹到20斤弹都造过,因此只能根据何汝宾的描述来互相印证,即重量在2300~2400斤之间的红夷炮。目前国内符合这个重量的红夷炮实物有两门,一门是收藏在广州市越秀山的崇祯十七年红夷铁炮,炮长260㎝,重两千斤内口径10㎝,另一门是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崇祯二年红夷铁炮,由两广总督王尊德监造,炮长258㎝重两千斤,口径却达到14㎝。取个中间数,2300~2400斤红夷炮当在12磅左右。这样由小到大,分别是2.5磅炮、5磅炮、8磅炮、12磅炮的配置组合。
厦门船
这么一算,很显然现实情况与《兵录》当中的炮舰记载大致相符。这也侧面印证了明朝水师在中后期,面对不同威胁之后的快速发展,从而迅速做出了相对应的调整,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果。这也说明了传统的海战模式已开始逐渐淘汰没落,侧舷舰炮慢慢成为主流。
而假如我们能按此发展下去,也可能会逐渐走上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之路。但随着清军入关,大规模海禁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中式战船的发展也就此嘎然而止了。而与此同时,英荷两国则已经率先进入到了风帆战列舰时代,后来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席卷欧洲,科技成果更是层出不穷!特别是军事领域,他们的军舰是越来越先进,这就是科技成果与军事的完美结合,这一点到了工业革命(即第一次科技革命)时期发展更甚,可谓是狂飙式的。而反观我们则愈加落后了,成为了当时的时代落伍者。以至于到了清末鸦片战争,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我们的水师根本不堪一击,那是一败涂地啊!落后就要挨打,这就是现实给你的一记响亮的耳光。没有别的出路,唯有创新与自强方能立足!
在攻陷君士坦丁堡的战役中?
没有乌尔班大炮,要拿命去叠平城墙才可能攻下来
谢邀,军迷通常有个误区,那就是棱堡万能论,不管穿越到哪个朝代,修个棱堡,射击没有死角,对方就是一个送。这可以说严重侮辱了古人的智慧,在冷兵器时代,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完整的城防体系比棱堡完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修复后的狄奥多西城墙城防体系君士坦丁堡的狄奥多西城墙就是典型例子,他实际上也是复杂的立体防御体系,包括三道城墙,后两道还有突出于城墙并高出城墙高度2米左右的城台碉堡。从而构成三层不同高度,并且无死角的打击网。
城台碉堡作用类似我国古代的城防体系的敌台马面,提供侧向火力。部分城台有出入口,前道城墙被突破后供其余防守军队向后撤退。掩护撤退后,抽去梯子或砍断就可以让追兵无法利用城台进入后道防御体系。同时防守方也可以利用这个通道补充兵力或追击扩大战果。
狄奥多西城墙的敌台高于城墙2米左右,其设计有点类似明代大将戚继光的空心敌台,这种设计在长城上非常常见。当城墙被突破后,守军还可以退入敌台,进行防守抵抗,配合增援部队赶到消灭敌军。在冷兵器时代,要想突破这样的防御体系,只有拿尸体去填。
我国古代的城防体系也是类似,羊马墙作为外部防御,有的还会修建简易的月城,与城墙形成高低火力。敌台、马面凸出于城墙提供侧向火力。城楼和角楼等作为最后支撑。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还都有类似战棚这种,简易临时性的活动棚屋,推出城墙增强侧向打击火力。不要侮辱了老祖宗的智慧,在冷兵器时代,这就是最强的防御体系。
乌尔班大炮唯一的问题就是,这种城墙防御体系设计时没有考虑大炮。西方的砖石城墙普遍厚度并不太厚,像狄奥多西城墙厚度只有3到5米,扛不了大炮轰击。
这才是棱堡取代石堡的原因所在,棱堡可以有效抵御大炮的轰击。较矮城墙可以降低大炮命中率,厚实墙体,以及成角度的迎弹面,可以弹开袭来的炮弹。在进攻方大炮失去工事破坏作用后,防守方的大炮却可以对攻城方造成成吨的伤害。
西安古城墙的横断面,夯土包砖最后一提,我国近代没有诞生棱堡设计,一方面是游牧民族铸炮技术差,一直到明末孔有德带着大量红夷大炮投降后,后金才拥有真正有威胁的攻城火力。另一方面,我国古代主要筑城法是夯土包砖,城墙本身拥有相当的厚度,并且夯土层吸能效果好,对于火炮的抵御效果本身要比西方的石制城墙好的多。还有老祖宗的攻城方法可不止强攻,比如郑成功对付荷兰人的棱堡是挖断水源……
努尔哈赤真的是被袁崇焕用红夷大炮炸伤而死的吗?
这个问题不错。关于这件事史学界确实有所争议,我也不敢轻易下定论。但我认为无论从史料层面分析还是从兵器杀伤角度分析,努尔哈赤的死大概率和火炮重伤没有关系,至少努尔哈赤中炮而亡的概率还是很小的(注意:对于此类历史事件我也不想一口咬死,就这样),我来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从史料层面上来看,说努尔哈赤因为炮伤身亡的证据是极不充分,无论是明清之际官方档案还是私著史书大部分都没有采信此说。首先来看看私家著述,稍微著名一点的都没有提及努尔哈赤在宁远中炮。
《国榷·卷八十七》:连发西洋炮,相持三日夜,敌气沮,退走灰山,斩二百六级。
评:谈迁对宁远之战的记载堪称保守,只说了极其简单的经过和斩级数目,根本未提后金军有高级人员死伤,更没有“建酋中炮死”这一类的情节,以这哥们的“捧明史观”,如果努尔哈赤真的被红衣炮击成重伤,非得大书一笔不可,而其没有将传闻写入,可见史笔严谨。
《石匮书后集·卷十一》: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
评:此书倒是明确提到了打到“黄龙幕”了,有可能是努尔哈赤的驻地,但后面也说只是伤到了一个“裨王”,显然不是努尔哈赤本人,至于那个“裨王”是谁?没有提及。但从此书毛文龙的传记显示努尔哈赤乃病死,“适当女直主病死”,并没有说明努尔哈赤病死与炮伤相关,也是证据不足。
《山中闻见录》:燔死锦衣名酋十余,杀千余人,晡时乃却走。
评:仅仅是“锦衣名酋”,没有提及努尔哈赤,证据不足。
《明季北略·卷二》:毙其锦服者十余人,所谓固山、牛鹿也。敌号哭舁尸而去。
评:原文说击毙的是固山、牛录这样的军官,不关努尔哈赤啥事。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五》:建州兵大举攻宁远,参政袁崇焕力御之,发炮击死无算,毙其帅长孙哈兔,斩级六百,建州兵从灰山解还。
评:努尔哈赤痛失一名叫“长孙哈兔”的军官,有可能是其手下在宁远城阵亡的二备御和二游击之一,并无提及努尔哈赤受伤。
至于明朝一方的官方奏报也没有明确提及努尔哈赤中炮身亡,可能有人会说努尔哈赤阵亡是不是袁崇焕吹出来的,但是实际上从袁崇焕的奏报上显示他根本就没提努尔哈赤中炮身亡这一嘴。以下是《三朝辽事实录》兵部转奏袁崇焕军报内容,大家可以看一下。
后来,努尔哈赤去世,袁崇焕听说“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疽,死于八月初十日”这个传闻后,一度认为是努尔哈赤诈死,“夫奴屡诈死懈我,今或仍诈,亦不可知”。
像徐光启为了吹红衣大炮的强劲实力,也只敢说红夷火炮一放,后金死了17000,只在敌军死亡数目上作文章,如果真的把努尔哈赤炸重伤了,把这写上去,岂不是广告效应更强?但是这就不敢乱吹了,敌军死亡数目还能糊弄一下,万一努尔哈赤还活蹦乱跳,岂不是很打脸,老徐可能想了想,还是不要乱写好。(此段有所脑补,见谅)
言之凿凿记载努尔哈赤中炮死亡的是朝鲜人韩瑗写的《春坡堂日月录》,据此书载努尔哈赤攻宁远时,他正在此地,上面对战斗过程还是大致可信的,而且还颇为详细。但是努尔哈赤如何受伤,韩瑗并未写明,只是在文末突兀的来了一句“奴儿赤先已重伤”,这就有点脑补之嫌了。而且其与袁崇焕同在宁远,如果努尔哈赤真的被炮击伤,能被他知道的消息,做为守城主将的袁崇焕难道就不知道吗?何以袁崇焕的奏报毫无显示,更让我怀疑有脑补的嫌疑。
说实话,朝鲜出于对清的极度愤恨,经常性的脑补额外情节已不止一两例了,比如说在崇德元年,皇太极坐稳了大汗的位置已经10年了,朝鲜人不知哪来的情报说清廷朝政不稳,有可能自相残杀云云,“今闻彼中已有相图之渐,此乃天亡之秋”,简直就是凭空想象。皇太极:“相图之渐?还天亡之秋?我怎么不知道?”
至于我国史书如《玉镜新谭》也有努尔哈赤被炮重伤一说,但是叙述极为夸张奇幻。比如说打仗的时候,天降流星,“其落地如天崩之状”,后金军集体震恐;努尔哈赤不仅重伤,还额外死了两个儿子;努尔哈赤死后,后金的汗位居然靠抓阄抽签决定。这确定不是脑补吗?这段的真实性可想而知。
总而言之,从史料角度看,明朝的官方奏报真心没有明确说努尔哈赤中炮受重伤,至于严谨一点的私修史书也没说努尔哈赤中炮受伤而死,所以这事真的是证据不足。
从火器运用角度来说,努尔哈赤中炮死亡的概率也很小,抑或是其受伤可能与炮击有关,但绝非致命。关于红夷炮的射程威力,史著很多,我一个外行人谈谈看法。首先,我们要摒弃西法党的吹牛之词,就比如说李之藻言红夷炮“二三十里之内,折巨木,透坚城,攻无不摧”,这个大家看看就好。
从《明清史料》看,清朝围锦州时候离城5~6里挖壕设营来看,红夷火炮的射程应该在这个距离以内,而《三朝辽事实录》里,努尔哈赤在从宁远撤退后就在距离5里的龙宫寺下营也可以印证这个判断,还有《平叛记》记载孔有德在登州城炮击明军也是“一发五六里”,可见红夷炮在城上布置其射程应该在5里以内。当然仅代表个人意见,具体射程学术界也无法统一,我就不再论述了。
至于威力无论是明清官方档案还是野史倒是很一致,被红夷大炮直接命中的后果很严重,大概率是直接死亡的,清军甚至能用红夷炮把塔山城给轰塌,就这威力什么甲都没用。
《平叛记校注·卷上》:在红夷大炮,铁子每个重六斤,触之即折,城垛尽倾,守垛者无处站立。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初八日始发炮,至初九日午时,城崩二十余丈,我兵由崩处登城。
如果努尔哈赤被红夷炮直接命中,那生还概率几乎为0,至少也应该会有缺胳膊断腿这样的重度伤残。但事实就是努尔哈赤在之后还亲率兵马长途奔袭内喀尔喀五部,还与科尔沁台吉奥巴进行会盟,在这个时候努尔哈赤还出城10里迎接奥巴,席间还热情的离坐行熊抱之礼,实在难以想象一个68岁的老者在被红夷大炮直接命中后还能幸存,或在受重大创伤之后还能完成这些行动。
当然,红夷火炮即便是不直接命中也会引起创伤,特别感谢@派大早的相关文章,让我吸收了相关知识,除了直接命中,造成创伤的因素还有两个:一是炮弹激起的各种碎屑;二是炮风。这两种创伤的严重程度根据受伤者所处的环境而杀伤效果各有不同,这个就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了,可能努尔哈赤离弹着点较远,只是受到了轻微炮风或者飞溅物的影响,但由于身披铠甲,其所受之伤绝非致命。因为在极近距离被弹风或飞溅物伤到,无论是被伤者的精神状况还是体质都会受到剧烈创伤,而从《满文老档》和《清武录》看,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后还能完成重大的军政活动可以推知,即便是他所受的伤即使与红夷大炮有关,也绝非致命因素。
而努尔哈赤的死因多半是自身的原因,首先、68岁这个年纪摆在这边,他自己已然是位老者。其次、在内政上自占领辽东以来,错误的实行民族压迫的政策,引起了广大辽东汉民的反抗,而其又一味的镇压,更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抗,陷入了恶性循环,这时又遭遇天灾,国内更加动荡,从《满文老档》的记载来看,努尔哈赤除了忧虑,对这个情况毫无办法。第三、年纪大再加上长途奔袭,使他原本就已经年老的身体雪上加霜。第四、与他一起创业的大臣在其晚年基本凋零,使其伤心过度。种种因素加起来,急火攻心之下,年事已高的努尔哈赤得了背疽,不治身亡,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更大一些。
引用文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三朝辽事实录》、《满文老档》、《明清史料》、《明经世文编》、《明史纪事本末》、《山中闻见录》、《袁崇焕集》、《国榷》、《明季北略》、《石匮书》、《平叛记》、《玉镜新谭》、《燃藜室记述》、《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